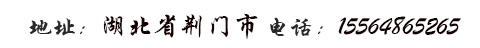徐栩宋代女性冠饰考
|
中国古代汉族女性最初并不戴冠,隋唐时期,贵族妇女才开始佩戴标志身份的花冠,如扬州隋炀帝与萧后合葬墓出土的铜鎏金花树冠,西安李倕墓出土冠饰以及李静训墓出土闹蛾扑花冠。 太平公主曾创制了一种名为“玉叶冠”的头饰,但除了名称并无其他相关记载传世。在唐朝人的笔记和诗句中还记载了“轻金冠”、“结条冠子”以及“碧罗冠子”,前两种推测是当时使用花丝工艺制作的头饰,后者则是用碧色织物制作的冠。 两宋时期,女性佩戴各种不同形状、材质冠子的形象大量出现在诗词、绘画和当时人的笔记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所写:“铺翠冠儿,碾金雪柳,簇带争济楚。”词中的“铺翠冠儿”就是当时中州妇女所戴的一种冠饰。 宋人吴自牧的笔记《梦梁录》卷十三“团行”一条提到杭州官巷有“方梳行”“冠子行”,制作出售极其工巧的冠子和梳,其中有名字号者曰“俞家冠子铺”、“沈家枕冠铺”,在街上游走的手艺人有做“补修冠”“修洗鹿胎冠子”的活计,更有小贩挑担售卖冠子。卷二十“嫁娶”条写聘礼中亦有“珠翠冠子”。 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诸色杂卖”一条也记载东京汴梁城里有“刷腰带、修幞头帽子、补洗角冠子”的手艺人。 从宋代皇后佩戴的花树龙凤冠到民间妇女所戴的各色冠子,它在宋代女性的首饰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休闲时可戴,盛礼时必戴,它既代表了佩戴者的身份,也表达了拥有者不同的审美情趣。 目前所见关于宋代女性冠饰的具体描述有两段,一段来自北宋王得臣的笔记《麈史》:“……始用以黄涂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或缀彩罗,为攒云、五岳之类。既禁用鹿胎、玳瑁,乃为白角者,又点角为假玳瑁之形者,然犹出四角而长矣。后至长 尺许,而登车檐皆侧首而入。俄又编竹而为团者,涂之以绿,浸变而以角为之,谓之团冠。复以长者屈四角而不至于肩,谓之亸肩。又以团冠少裁其两边,而高其前后,谓之山口。又以亸肩直其角而短,谓之短冠。今则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棱托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今则皆以珠玑缀之。其方尚长冠也,所傅两角梳亦长七八寸。习尚之盛,在于皇佑、至和之闲。” 另一段来自成书于南宋的《燕翼诒谋录·卷四》:“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议者以为妖,仁宗亦恶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训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两段文字都提到了妇女所戴冠子的形状、材质和名目,以及随着社会发展和官方禁令而产生的变化——从最初没有特殊规定的漆纱制,再到加以金银珠翠和彩花装饰,再到鹿胎、白角、玳瑁……也此反映出社会经济对女性装饰的影响。 本文尝试从时间和材质出发,配合绘画及出土文物简略划分每种宋代女性冠饰的流行时间。 宋代女性冠饰的材质 1、金、银 目前出土的宋代女性冠饰实物皆为金、银质,如安徽舒城县三里村宋墓出土银山口冠、祁门博物馆藏宋代银冠、安徽博物院藏安庆市棋盘山范文虎夫妇墓出土金冠、湖南华容元墓出土银冠,其材质都与宋代笔记相符。 安徽舒城县三里村宋墓银冠(仅见发掘简报) 祁门博物馆宋代银冠 范文虎夫妇墓金冠 湖南华容元墓银冠 2、鹿胎之革 “鹿胎之革”是尚未出生的幼梅花鹿之皮,古人言其“皮毛鲜泽,文采可爱”,在唐代用以制作道人的冠饰,男女道人均可佩戴。唐代花蕊夫人诗云“老大初教学道人,鹿皮冠子澹黄裙。”一直到宋代,鹿胎冠都是道人的装束,如宋诗《走笔赠仙姑》中有一句“鹿胎冠子青纱袍,神风清峻真仙曹。”即描写了一位戴鹿胎冠的坤道。 鹿胎,图源网络 南宋王利用《写神老君变化十式图》中佩戴鹿胎冠的道人形象 或许是因其新奇难得,宋时多被“臣庶之家”剖取来制作冠饰以攀比炫富,还有命妇戴着直入大内。俗家女性开始佩戴鹿胎冠,与宋代崇尚道教的风气不无关联。 北宋王之道所做《浣溪沙·赋春雪追和东坡韵四首》中有“鹿胎冠子粲歌珠”之句,想来此样冠子也被歌姬佩戴。 但采捕鹿胎不仅危害幼鹿,更会导致大量怀孕母鹿死亡,因其过于奢靡残忍,有宋一朝皇帝屡发禁令,甚至宋仁宗时还有对戴鹿胎冠者和制造鹿胎冠者共同罚款的上谕。但这些禁令收效甚微,鹿胎冠一直流行到南宋末期才真正消失。 淄博窑遗址出土的金代戴冠三彩侍女俑中,就有一例冠上装饰类似鹿胎纹的抱婴儿妇女形象。山东位于宋辽金交界,鹿胎冠这种 品流行到此也是可以想象的。 淄博窑的烧制时间为北宋,与白沙宋墓壁画时间相若,此冠的佩戴效果也与白沙宋墓壁画中的女性形象相似。另,白沙宋墓壁画中的侍女所戴之冠,花纹类似矩形拼接,或许是用彩色罗帛裁剪拼缀所制。 淄博窑带鹿胎冠女俑 白沙宋墓m2梳妆图 3、白角 “白角”的解释是磨光的白色牛角。 北宋周煇所著《清波杂志》“垂肩冠”一条中记载到“皇祐初……宫中尚白角冠……”。 北宋刘斧的文言小说总集《青琐高议》中有《温泉记·西蜀张俞遇太真》一篇,记述张俞游骊山遇见已经成仙的杨玉环,两人宴饮时,仙子问张俞如今妇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张俞回答:(如今的妇人)多用白角作为冠子,金珠作为饰物。(原文:“仙谓曰:今之妇人首饰衣者如何?俞对曰:多用白角为冠,金珠为饰,民间多用两川红紫。”) 由此可见,在宋时“白角冠”是因材质而名,并非特定形状。北宋诗人梅尧臣在《当世家观画》一诗中也有“白角盈薄垂肩冠。”之句。 宋词中还出现过“水晶冠子”一词,按照水晶的硬度和材料获取难度,笔者更倾向于这是词人的比喻,实际应为透明角冠 但这种冠饰未见出土文物,制作方法也已失传,现存有羊角灯制法,依法炮制白羊角,其成品薄透轻盈,或可借此想象白角冠之样貌。 4、鱼枕 鱼枕是青鱼枕骨下方咽喉部用来辅助压碎螺蛳等硬质食物的角质增生,外表粗糙有鱼腥味,经打磨抛光后呈 色,触手温润,现俗称“鱼惊石”,做饰品用。《燕翼诒谋录》中记载有用“鱼枕”做成的冠子,亦写作“鱼魫冠”。 苏轼有《鱼枕冠颂》,写此种冠子晶莹剔透,材料由剖鱼而得,制作方法是“汤火就模范”。但笔者曾经尝试用开水煮过鱼枕骨,只能使其略微变软,无法到到制作冠饰的目的。 5、玳瑁 玳瑁,即玳瑁龟的甲壳,磨制后有特殊花纹,莹润通透,此材质制成的梳子在《捣练图》中有描绘,它出现在宫娥鬓上,不过一指余长两指来宽。但玳瑁制冠子目前未见绘画形象,亦无实物出土。 6、象牙 大象的牙。和鹿胎、玳瑁一样是 的动物制品。其成品应该是象牙白色,但目前亦未见绘画形象和出土文物。 7、竹 此材质也为《燕翼诒谋录》所载,以竹编织成团,再涂以绿色做成“团冠”。此种冠子亦无出土文物,但以竹篾制作冠胎的工艺一直到明代仍在使用,定陵出土的四顶凤冠均以竹篾为胎。 宋代女性冠饰的名称与形象 北宋早期 北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写到曾经有人发现了一幅晋代漆画,画中的妇女头上戴着巨大帽子,就像当时北宋妇女所戴的垂肩冠,形制是两翼抱面,下垂及肩。垂肩冠亦不见于绘画,但有陶俑呈现了佩戴垂肩冠形象。 金三彩仕女俑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 新津县文管所藏北宋元丰三年x岁女陶俑 如上三张图片可以看到垂肩冠的整体形状和佩戴状态。 比垂肩冠四角略短,“长者曲四角而不至于肩”的冠子称做“亸肩冠”,两翼仅下垂及耳。宋代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写宋徽宗 次见到李师师时,远远望见诗诗隐在帘下,头上“亸肩鸾髻“宛如仙女。也是那年正月十五夜,城中百姓齐往端门看鳌山,佳人们头戴亸肩冠儿,鬓边插禁苑瑶花,星眸流转比春桃更为娇艳。 如下图仕女俑所戴,推测为“亸肩冠” 金三彩仕女俑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 还有一种几乎与肩同宽的冠子“形状出四角而长”,其长度可达到到宋尺二、三尺,佩戴者登车时都需要侧身而入,防止被车门卡住。此样式名“等肩冠”,也可以在淄博窑出土的侍女俑中看到。 金三彩仕女俑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 另观此类戴冠俑,冠子中间或有一圆球形装饰,或是一个圆孔似供插戴簪子。这个簪子的功能是固定冠子。 此类圆球簪,有现藏安徽省界首市博物馆之宋代簪做参考。该簪下半部分残损,上半部分为单股簪,簪头为空心金属球。 安徽界首博物馆宋代球簪 团冠 “编竹为团”的团冠,后期材质有所改变,仍保留了形状。单独佩戴在头顶正中,或插球簪以固定。 安徽南陵铁拐村北宋墓出土女乐俑 洛阳古墓博物馆妇人启门图 河北唐庄宋墓壁画 白沙宋墓壁画 山口冠 北宋早期末段,出现了“以团冠少裁其两边,而高其前后”的山口冠。将团冠前后加高收束,两边更凹,就成了这个样子。 安徽舒城县三里村宋墓出土的银冠即是山口冠,晋祠这尊团冠侍女和《招凉仕女图》中左侧妇女也佩戴了山口冠。 程垓《醉落魄赋石榴花》写“透明冠子轻盈帖”,而这位仕女恰佩戴了一个透明的山口冠。 《招凉仕女图》 晋祠团冠侍女(南壁西起第五) 晋祠这尊团冠侍女头上的红色带状物,即是北宋代女性另一种头饰——“头须”。 一种异形山口冠,佩戴者穿大袖衫捧横帔,推测为礼服冠。 短冠 亸肩直其角而短,谓之短冠。从绘画和陶俑形象分析,应是按佩戴者身份,前后插塔形发簪、球簪或不插发簪。 白沙宋墓 亸肩直其角而短,谓之短冠。 并桃冠子 宋刘子翚(抗金将领、南宋理学家)《汴京纪事二十首》:并桃冠子玉簪斜。 《苕溪集》:宣和宫女头作冠,双桃相并,谓文并桃冠,人以桃音逃,为今日之谶。 此冠形状为两桃相并尖头朝外,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说它大致出现于北宋政和年间,佩戴者有乐伎也有普通妇女。 从现存图像资料中佩戴类似并桃冠的妇女形象来看,这种冠饰可能一直流行到南宋末期,并被元初的画家所记录。 元张雨《题倪瓒像卷》 元程启《耕织图》 甘肃陇南徽县出土宋代女俑 南宋 朵云冠 贺铸《蝶恋花·小院朱扉开一扇》:朵云冠子偏宜面。 “朵云”一词仿佛是形容云朵汇聚,又仿佛是形容头冠的形状小巧,如一朵云一样纤巧轻灵。 此冠无明确解释,无对应形象。期待日后考古成果。 下附图皆为佩戴蚌壳形冠饰的南宋女性形象。 元程启《耕织图》 南宋佚名《蕉荫击球图》 南宋陈清波《瑶台步月图》 南宋陆仲渊《十王图》 贯穿两宋的“花冠” 宋人爱花、赏花、簪花,将鲜花融入生活和礼仪的方方面面,女性用鲜花装点发髻,也用各种材料将发冠做成花的样子。 唐代有一句《沧州语》:“不戴金莲花,不得到仙家,”后蜀皇宫的妃嫔则做“莲花冠子道人衣”之装束,晋祠仕女中也有头戴莲花冠的形象。 佩戴莲花冠有道教意味,与当时整个社会崇尚道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晋祠花冠仕女 除了莲花形状,还有下图这样花瓣层叠的冠子,比之仙气十足的莲花冠更多了几分轻盈娇俏。 白沙宋墓壁画,宋元符二年 南宋《女孝经图》中戴花冠冠的两位女性 龙凤博鬓冠 《宋钦宗皇后坐像》 广胜寺壁画中的太阴星君 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朝元图》中的金母元君,冠子后面像翅膀一样的结构称为“博鬓”。此制度始于唐代,《旧唐书·舆服志》:“内外命妇服花钗,施两博鬓。”宋明承袭了这个制度,只有皇后才可以佩戴有“博鬓”的冠,上饰龙凤,尽显皇家气像。 这是中国古代妇女等级 的冠饰,在宗教壁画中也只有高级女神仙才能佩戴。 结语 两宋时女性所戴的冠子材质各异,并非独立出现,也无明确时代划分,甚至同一时期流行着许多不同形态的冠子。 具体来说,北宋的冠子高耸阔大,无论形状如何都戴在头顶,且不封顶;南宋的冠子内敛精致,佩戴位置逐渐推至后脑勺,顶部封闭。我们可以通过冠的佩戴位置和服饰来确定大致时间。 徐栩, 届中央电视台“中国国宝大会”全国第七,中国博物馆协会个人会员,乐清历史学会会员,乐清古琴研究会古琴专业委员会员。 *************** 浩按:a、按语和正文的关系,我认为可用余嘉锡先生语喻之,“紀氏控弦引滿,下雲中之飛鳥,余則樹之鵠而後放矢耳。易地以處,紀氏必優於作《辨證》,而余之不能為提要決也。”未敢拟于前贤,然理则一也。 b、徐君好学深思,于服饰一道多寻之于古籍,验之于考古,亲手拟做以求正识,未尝滞于寻章摘句之不求甚解,叠床架屋之概念堆砌也。自然,概念之剖辩亦非易事,余论“凡”、“舟”本一字,多蒙然未明者。其实甚易。“舟”作偏旁之字,甲骨文中多以“凡”或“凡”\“舟”的两种形式出现。“凡”这个构件全部被“舟”这个构件混讹代替是很难解释的, 的可能就是“舟”这个构件比“凡”这个构件更能明确表意,这种表意只能是同意或意近,如用“火”替代“灬”(另,温少峰先生有证甲骨中凡有帆意思)。所以“凡”没有成为部首,而“舟”成为了部首。而后世隶定“舟”作为偏旁的字,在甲骨文中皆会意字,但作“凡”就很难会意,这就不得不对于每个作“凡”而不作“舟”的构件强解。但对每字强解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凡”、“舟”皆出现在甲骨一期,但可以推断二字本一无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uiyuncaoa.com/cycpzff/8964.html
- 上一篇文章: 贴墙站立热量咔咔地掉,周末我也来加练了
- 下一篇文章: 美拍惠州小垦丁,住进海龟自然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