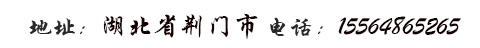南渡客15
|
即使说话之人是孟语,而黎衡也已然习惯了听从他的建议,他还是疑心听错了,又在良久后黯然道:“要是没有你,连这一千石稻谷,也讨不来。” “这话不对。” 黎衡苦笑:“杨刺史为何又允了?” “县令 次求援,为的是县内百姓的生计。区区一千石稻米,刺史怎能让县令空手而归。” “你方才不是说……”黎衡刚觉得自己明白些,此刻又糊涂了。 “刺史离百姓太远,离县令却近。”孟语略一顿,缓缓说,“明年开春米贵之时,县令如果还想再向州府求援,恐怕难以如愿。其实高县尉所言不差,这个季节靠山海之馈赠,是可以熬下去的。” 短暂的沉默后,黎衡怅然又道:“你不必刻意宽慰我。杨刺史上午在堂上勃然大怒,见过你,就拨了千石稻谷。百万钱值多少金?有千金没有?” “差得远了。一两金要是在帝京,约可兑钱八千至一万二。岭南金价更高,一两金至少兑钱一万五,算来百万钱还兑不得百金。” 黎衡勉强一笑:“哦,我以为你的面子当值千金。” “杨刺史发怒,不全是县令求粮。石潭受灾,春林也难以幸免,赈灾不仅是州府的职责,更是仁政所在,县令这一上禀,虽是无心,还是驳了他人颜面。杨刺史不得不发怒。县令不必挂怀。” “灾情这样的大事,难道也要等州府施恩?” 孟语终于又笑了,却是说:“粮已要到了,县令这一顿委屈,抵了百万钱。” 被孟语的微笑所感染,黎衡不再追问,长长叹了口气,轻声说:“既然刺史同意拨粮,我们也尽快返程吧。” “今日赶不回石潭了。”眼看黎衡露出失望的神色,孟语说,“你如不愿在春林再住一晚,动身也无妨,有个地方可以过夜。” “是不愿意。就算非在春林再住一晚,刺史官邸我也不回去了……你说可以过夜的地方,在哪里?” 出春林城后,孟语领着黎衡向更南方行去。这是与回石潭的路彻底相反的方向。黎衡对春林一带本陌生,这下更不知道孟语会把他带向何处。但因为身旁之人是孟语,黎衡按捺住好奇,跟着他沿着因降雨而松软的道路又骑了不到十里地,渐渐的,风中多出了人声和潮声,转过一个平平无奇的路口,黎衡呼吸一滞,仓促地勒停了马。 撞入视线的,自然是铅灰色的天空和海,狭长的海滩上,劳作的人群如蚁群般聚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一件事——将沙土或海水肩挑手扛地运至离海稍远处的几个深坑里,循环往复,看不到起点也仿佛没有尽头。 “春林能成为琴州的治所,就是因为东南的这处盐田。” 人活在世上,总要吃盐,可盐从何来,黎衡真没见过。他默默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分明盐在哪里,或从何处来,目光所及处,除了衣衫褴褛的苦役,就只有海水和沙土,他只能向孟语救助:“盐呢?” “他们所运的盐沙和海水,就是盐的原料。土里有盐,一担盐土在春秋需浇八担海水,夏季则要十担,由此滤出卤水,然后再上火,煎煮时火不能断,视卤水的浓淡,短则四五日,长则一旬,待卤中的水煮干了,就成了盐。本地人称作‘煮海’。” 有了孟语的解说,黎衡这才稍微看出点门道,不免感慨:“原来如此辛苦。那一担盐土,又能出多少盐?” “听说至少要五六担土,才能出一担卤。” “无怪叫煮海。”但黎衡找了半天,视线所及处也没看有人生火,“是不是夏季太热,煮不了盐?” 孟语看他一眼,摇头:“除了正月的几日,一年四季不停。要是雨季雨水太烈,也会暂停几日。” “……你也在此地劳作过?” “没有。在盐田服役的都是重犯,只比送往鹘岛略好些,我尚不至于如此。” “……那时你在做什么?” 话虽然问出了口,心依然悬在高处,可黎衡并不懊悔这下意识的提问。 “我在乐枫岭伐木。春夏秋三季送到这里煮海,冬季除了送来煮盐,有时也会留在山中 ,送到石潭和春林的官府,供他们过冬。” 过了片刻,他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了一点疼痛,来得太迟,以至于都不合时宜了,甚至让他生出窘迫。仿佛一根过于尖锐的木刺,刚戳进去时还来不及让人有所察觉,等意识到扎进了一根刺,它已经钻得太深了。 黎衡从未和孟语直白地谈及后者在琴州的过往,哪怕他已然肯定地知道,孟语当年的境遇,与自己亲眼所见的许多人并无二致。不去细问,并非他不渴望知晓关于孟语的一切,而以他的身份,本就可以举重若轻、公事公办地“过问”。 黎衡已经不太能确定为什么自己一再地放过这些机会。又这么容易地问出了口。对着孟语这样的人,不问是容易的,他是如此的可靠、得力,无需坦承旧事就能获得信赖和倚重。不知道他的过去也可以得到他的一部分,又或者,正是靠着给予自己的一部分,让黎衡选择不去过问他的过去。 随从们不是被打发去向督工的盐官告知他们的到来,就是远远地守在另一侧。黎衡又转过头,看着远处滩上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片刻也不得停息的劳役,轻声说:“我没有向高满询问你在春林的旧事。我没问过任何人。” “我知道。” “以前我想过……”黎衡顿了顿,像是要聚集一点力气,“如果有一日你我能交心,你会告诉我。我不会再问了。不过,为什么带我来看这个?” “你不愿意住在春林,又回不去石潭,看一看又何妨?这本来也是琴州的一景。” 黎衡摇头,笑着叹了口气:“你告诉了我,以后我再看到他们,就会忍不住想,里面是不是有年轻的你。” “……天下各州,每到岁末要向圣人进奉本地的特产。琴州的贡品只有两种,均是先帝时钦定的。一是眼前这块地所出的盐,一是细葛布,而道内其他州,上贡的则是珍珠、玳瑁、沉香之类的珍奇。” 若是以前,黎衡听到这番话,会以为接下来的话是颂圣。他没有急于出声,耐心地等孟语说下去:“只是无论盐或葛布,发来琴州的犯人,即使不分昼夜劳作,仍有不能凑齐之虞。所以一年四季,无时无刻,男子都在挑海煮盐,女子都在种葛织布,琴州不远万里上呈的,自然也不是盐葛这等平平无奇之物,而是罪臣的苦役和悔改之心。你如不能明白这一层,永远会触怒杨刺史。更有甚者,除非免官,再难离开此地。” 黎衡垂下双目,淡淡说:“我不来此地,就不会遇到你。你不必担心,此事上我虽然谈不上经验二字,但到了那一日,无论是你我谁离开琴州,日后又是否能相见,起因既然在我,善后也在我。不会教你为难。” “你想如何善后?” 见他又要笑,黎衡禁不住又要耳热,他忍下不快,字斟句酌地说:“……到时自见分晓。但你我之事上,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应允。” 孟语真的笑了:“黎郎君当真慷慨。” 黎衡勉强也笑了笑:“我想了许久,总觉得不知从何说起,没想到竟是这样说的,天时地利全无,你要觉得我轻浮,我别无二言。” 在心头徘徊已久的话一旦说出口,黎衡也并未觉得松弛多少。孟语没有接话,为此黎衡甚至觉得庆幸。他没有再说下去,格外用心地看了很久沙滩上诸人劳作,直到先前去传话的差役领着督差前来迎接,盘踞在两 的沉默才告一段落。 盐场常年有人值守,刺史府也定期有人巡查,不缺住宿之处。黎衡前几日在杨凌宅邸一直歇息得不好,按理说本该极困顿了,但没想到依然无法入眠。听了不知道多久的浪潮声,他默默起身穿好衣袍,敲开了隔壁的房门。 “不习惯潮声?”孟语披衣举着灯,打量了一眼黎衡,问道。 黎衡随意点点头:“或许吧。” “是我疏忽了。石潭和春林城中都听不见潮声。” “不打紧。我想去海边看看。你指个方向给我吧。” 极短暂的沉默后,孟语说:“夜间的海边与白日大不同。不熟悉的人孤身前往不妥。我与你同去。” “也好。” 孟语换好衣裳,又专门找到护卫要了两盏防风的灯笼。听说二人要去海边,护卫们均大惊失色,劝他们天明涨完潮再出门。孟语说:“我过去在琴州住过,知道潮汛。现在潮水正低,去去就回。” 黎衡不说话,神色却异常坚决,众人劝了半天无用,又不敢忤逆临县的父母官,只能反复提醒了一番定要提防夜浪、不可离海太近云云,十二分不情愿地把黎衡和孟语送出了门。 日间天气阴沉,夜里竟清朗了许多,半轮月亮挂在天边,照出海浪与滩涂的分界,好似一条蜿蜒无穷的丝线。黎衡心愿得偿,觉得畅快之极,不顾黑夜和沙滩难行,脚步很是轻快,仿佛只一眨眼的光景,海水已经打湿了他的靴子。 孟语拉住了他,轻声说:“不要再往前了。” “水还浅得很。”黎衡甩开他的手,弯腰脱下鞋袜,用力扔到离海更远的方向。微凉的海水像争先恐后的鱼群那样扑上他的脚趾和脚背,有的还飞溅上他的脸颊,咸苦的味道之外,还有一股难以形容、但绝不教他讨厌的新鲜气味。天地间充斥着波涛声,很清晰,又很轻,是黎衡从来没有听过的声响。 “现在是夏天,潮和太阳一起来,夏天的潮水上得很快,等到觉察,就晚了。”孟语耐心解释完,语气忽然一变,柔和之外多了一分好奇,“你想看什么?” “不知道。”感觉到孟语再次挽住了自己的胳膊,黎衡没有再挣脱,他诚实地回答了孟语的问题,“我躺在枕上时,觉得它在叫我。白天时觉得壮阔,现在又觉得森然。它太大了,你我就像盐粒。但就是想看一看晚上是什么样子。你不同来,我也是要来的。” 他不可抑制地想起初见的那天,陌生的乡野间一切都大得失常,直到眼前之人踏雨走进凉亭,天地万物的尺寸才重新变成了自己熟悉的。 而此刻,孟语的侧影又是如此高大,影子溶进浪里,再随着浪,轻柔地握住黎衡的脚踝。微弱的痒意拉回了黎衡的心绪,他轻轻踩住孟语的脚背,然后靠上前,附耳将方才所想告诉了他。 两个人都灯笼的光团在一起,孟语的脸笼罩在摇曳而模糊的光线下,依稀流露出一线忡怔,这让黎衡蓦地生出了玩笑心,很快的,它又变成了别的东西。 在浪潮再度拂过脚背的一刻,黎衡踮起脚,十分迅速、又生疏地擦过孟语的鬓角,笨拙地贴住了他的脸颊。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uiyuncaoa.com/cycyfyl/8858.html
- 上一篇文章: 范可新被依靠,而不是依靠
- 下一篇文章: 金瓶梅第五十九回官哥儿死亡是一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