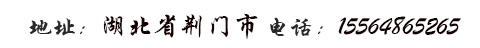沦亡帝王,千古词人丨李煜词浪淘沙赏读
| 白癜风诊疗目标 https://news.39.net/bjzkhbzy/180423/6185379.html“亡国君主,千古词人”,这八个字大约就能概括李煜的一生,大家都知道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了”-------然则后主词传唱千古、影响深远,但鲜有人知其词的好处在哪、如何赏析。借此,笔者就从后主的《浪淘沙丨往事只堪哀》入手,谈谈后主究竟是凭借什么,纵横千古词坛的。浪淘沙五代·李煜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今日的秦淮河后主词久负盛名,但实际上能从纯文学方向赏析的点并不多-------早期的花间遗风尚且能从字句风格入手: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菩萨蛮》如这种充满着南唐花间遗风的词作,其实除去状物细腻,辞色旖旎之外,是看不到更多的“思想厚度”的------这也是当时词人的通病(或者说是词体的通病),我们看李煜这个时期的词作,就当成《花间集》来看是没一点问题的。然自秣陵旧事之后,李煜的词得到极大的升华,这个升华是“思想”上的升华,但归到作词上,李煜只是用最简单的平铺直叙-----这却是最难鉴赏的词家作品了(文本式赏析除外),甚至于这种词李煜写是好词,换个人就是三流作品。浪淘沙这个调子,非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情不能写。李煜两首《浪淘沙》皆是在故国生涯和囚禁生涯之中转圜凄凉,所以尤为触目惊心。这首《浪淘沙》依然是后主被囚于汴京时,感念秣陵而作。沈际飞在《草堂诗余续集》中表示这首词“读不忍霓”----但其实这么写只有李煜才能让人“读不忍霓”,为什么?“光环问题”。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这个堪哀的“往事”与我们不一样,从皇帝到阶下囚,从“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的歌舞承平,到本词中的“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这种反差是我们能想见的,甚至是不需要修饰就能直接给人极大的“哀致”触动。陈廷焯在《大雅集》中点评曰:“起五字极凄婉,而来势妙,极突兀”这个凄婉最大的根本是来自人物(李煜)地位变化带来的,所谓来势也并不妙,就单单的自写境况而已,设身处地,任谁在这种情境下不会处境生情?不会说一句“往事不堪回首”?此词确是好词,但并非是结构章法如何妙、如何神来之笔,而是李煜的这种“帝王身份却带着空想式文人”的气质表达的淋漓尽致-----看不到英雄陌路的悲凉,却只看见一个可怜的富贵公子,在孤独中怀念彼时的歌舞升平:秋风庭院藓侵阶-----秋风萧瑟,苔藓满台阶,这就是门庭寥落;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而囚禁生涯中,想的也只是“终日谁来”,想的是有人来“看望我”,这种脆弱的心态和他的帝王身份的冲突便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可悲,可怜,可恨而已。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下篇从眼前事深入过去,“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便是呼应上片的“往事只堪哀”,刘禹锡有首怀古诗可以参见一二:刘禹锡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缅怀“王气黯然收”、“铁锁沉江底”,而李煜直接自述身世便愈发悲慨。但转过来,“金戈铁马”之气转瞬即逝,接下来又是“词人本色”:“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月色之下,回首秦淮河畔,想见却不曾见当年的“玉楼瑶殿影”在秦淮河上迤逦生姿,不过是更生凄咽。后主词在这个时间段(被俘虏),已经没什么笔法、也不需要笔法来提升文学的艺术性了,只单单将凄惨的身世照实写下来便是“千古词人低头”的境界。但我们说李煜词好,是好在这种文人式的天真和身世的纠葛矛盾带来的奇特凄美之感。陈廷焯:后主词思路凄惋,词场本色,不及飞卿之厚,自胜牛松卿辈。[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此言真一针见血,友人有句关于知人论诗的话叫做“以诗交人,两不可知”-------这句话对谁都合适,但独独对李煜不可,如果要真的读出李煜词的那种特质,非“以词交人”不可。总而言之,李煜词技艺只在于“真”。在大周后死之前,李煜词无非止与《花间词》诸家并举,逃不过侧艳之词的路数;大周后去世到李煜死时,他的真性情词才卓然立于五代之中,横看人间。但是这种高度,背后的代价不可谓不大:1.当皇帝还被俘虏了。2.有老婆还被人睡了。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鋹,令纵观,谓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吴王。《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列传第二百三十七》{小周}后岁时例随命妇入宫朝谒,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驾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南唐书》小周后剧照到此,我们除了感叹一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边工”之外,更多的犹是对这位“翰林学士”的可怜,可恨之感罢了。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开宝四年,煜遣其弟韩王从善朝京师,遂留不遣。煜手疏求从善还国,太祖皇帝不许。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uiyuncaoa.com/cycyfyl/11443.html
- 上一篇文章: 洪洞一神柏,已存活了3400年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